文/天津財經大學法學院 趙天水 郭澤
為嚴格落實食品安全責任,《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了懲罰性賠償。該制度與傳統民法之填補性賠償在作用、構成要件、賠償額以及效力來源等方面均存有不同。在司法實踐中,須注意對于“明知”的判斷。但真實有效的行政許可可以作為否定經營者主觀明知的理由。此外,對于職業打假人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2016年8月31日,劉某于蘇寧易購公司(以下簡稱“蘇寧”)網站購買了單價49元的某品牌麥片12盒,享受5元優惠后實際支付583元。該產品外包裝標注的配料注明產品中含有亞麻籽。因亞麻籽在我國并不屬于可以添加到普通食品中的中藥材,劉某認為蘇寧銷售涉案麥片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以下簡稱“《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之規定,遂起訴要求蘇寧退貨退款并承擔價款十倍的懲罰性賠償。蘇寧以其信賴行政機關的檢驗檢疫證明為由主張抗辯。最終法院認為,蘇寧主觀上并不明知所售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對劉某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另查明,除本案所涉商品,劉某分6批購買了本案相同商品共計355盒,總價15536.8元,分別提起7個訴訟要求蘇寧承擔十倍價款賠償,共計155368元。
二、學理分析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一千元的,為一千元。”基本上,我國一直遵循“賠償以填補損害為原則”這一傳統民法理念。而損害賠償之目的在于通過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使其恢復到受損害之前的圓滿狀態,即賠償應當與損失相稱,不能超過實際損失,防止受害人從損失中獲利。考慮到為懲罰和遏制嚴重的食品安全違法行為,我國立法突破了傳統民法理論的限制,通過設立《食品安全法》引入懲罰性賠償機制,加重惡意食品經營者的違法成本,促其嚴格落實食品安全責任。
1.懲罰性賠償與填補性賠償
懲罰性賠償制度源于英國判例法,又稱示范性賠償或報復性賠償。其與填補性損害賠償主要區別如下,第一,從作用上講,懲罰性賠償兼具懲罰和賠償兩種功能,同時附帶對潛在違法分子的威嚇。而填補性賠償,旨在填補受害人遭受的損失,使其權利恢復至損害發生之前的圓滿狀態。第二,從構成要件上講,懲罰性賠償的適用需要同時具備兩個要件:客觀上具有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的行為;主觀上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而銷售。可見,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不單純以損害的實際發生為前提,賠償的數額不以受害人的實際損失為限。填補性賠償的適用以加害人過錯、實施損害行為、損害后果以及損害的發生與后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為必要條件。第三,從賠償數額上講,懲罰性賠償對經營者苛以成倍的賠償數目以實現懲罰目的,而填補性賠償以填補受害人實際損失為限。通常,懲罰性賠償的賠償數額遠高于填補性賠償。第四,從效力來源上講,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數額的確定應當依據法律的明文規定,不得擅斷。即使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了帶有懲罰性質的賠償條款,一般也不應認定為懲罰性賠償。而填補性賠償的法律效力來源則不限于法律之明文規定。
2.懲罰性賠償之正當性依據
如上所述,與填補性賠償不同的是懲罰性賠償的功能在于賠償所帶有的懲罰性質。在食品安全領域,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對象為不安全食品的生產者和經營者實施的加害行為。而適用“懲罰”的前提在于確定加害人主客觀兩方面是否具有不法性。若生產者、經營者知曉其生產、經營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便可直接認定其具有主觀故意的不法性。另外,生產者、經營者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沒有盡到必要注意與審查義務時,則可推定其存在重大過失的不法性。該不法性亦構成懲罰性賠償的懲罰的正當性基礎。
考慮到食用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會對受害人的身體造成損害,加害人應當承擔由此引發的醫藥費、護理費和誤工費等必要費用。同時,加害行為還可能對受害人造成精神損害。由于精神損害不易評估,通過懲罰性賠償亦可救濟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另外,受困于醫學發展的局限,許多加害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被證實,這給適用填補性賠償的適用增加了困難。而懲罰性賠償不受考證因果關系的限制,只要客觀上存在生產與經營問題的事實即可主張,因此,可極大減輕受害人的證明義務。
另外,學界通說認為,懲罰性賠償亦帶有遏制功能。即懲罰性賠償可以威嚇、阻卻潛在的加害人,通過加大違法成本對個別加害人施予懲罰性賠償可以儆效尤。鑒于食品行業關涉公共安全的特殊屬性,只有大幅提高違法成本,才能真正發揮遏制同類行為的作用。此亦即懲罰性賠償的“示范性”作用。“示范性賠償”的別名也來源于此。
最后,懲罰性賠償亦具有激勵作用。食品安全問題中的諸多受害人難憑一己之力救濟因食用不合格食品而遭受損害。此外,高昂的訴訟成本和漫長的訴訟程序也會影響受害人主張權利的積極性。而懲罰性賠償可激勵受害人積極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合法權利,從而達到倒逼生產經營者嚴格履行食品安全責任,維護食品公共安全的目的。
三、司法觀點
影響本案最終判決的要點有二:
第一,作為經營者,蘇寧依法查驗了涉案商品的入境貨物檢驗檢疫證明、進口貨物報送單、供貨商的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證、食品流通許可證審批文件及資質材料,已經履行了經營者的法定審核義務。在浦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對涉案進口麥片已經作出“檢驗合格準予進口”的行政許可情況下,蘇寧基于對行政機關檢驗檢疫證明的信賴,購買并銷售涉案進口麥片,不能認定蘇寧主觀上具備《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的“明知”。如上所述,“明知”即可理解為經營者明確知道卻依然銷售之“故意”,或者經營者有知道之義務但出于“重大過失”而不知道的兩種情形。本案中,雖然蘇寧主觀認為“所售商品符合國家安全標準”與客觀事實不符,但蘇寧這一認識,在主觀上并不具備“故意”或“重大過失”,因此,不符合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前提。
第二,在本案中,值得注意的另一情形是,劉某曾多次反復購買相同涉案商品。其購買行為并不符合基于“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立法目的,在本質上屬于職業打假人的知假買假行為。所謂“職業打假”,是指不以日常使用為目的,專門購買不符合質量標準的商品,以訴訟手段要求生產經營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從中謀利的行為。現階段法院一般不支持職業打假人的賠償請求。究其原因在于,其一,職業打假人不是出于生活消費目的購買商品,不符合大多數懲罰性賠償條款要求的“消費者”主體身份。其二,如果支持其適用懲罰性賠償,會助長惡意造成損害后索取高額賠償的社會不正風氣。
四、實務應對
綜上所述,懲罰性賠償兼具賠償、懲罰、遏制與激勵等功能,其賠償數額也遠超填補性損害賠償。正因為如此,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會受到嚴格的實體法和程序法上的制約。結合本案而言,《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生產經營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藥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中藥材的物質。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中藥材的物質目錄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會同國務院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制定、公布。”由于法律明文規定了食品中可以添加的物質,而依法生產經營又是每一個法律主體的義務,因此,不履行上述規定之義務即可視為違反本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的規定,構成所謂的“明知”。但是,如本案所示,若經營者有合理證據表明其信賴所經營食品中的添加物質符合了國家食品安全標準的,依據信賴利益不得侵犯原則,應當否定其主觀上狀態構成本法第一百四十八條所言之“明知”。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實務中,在食品中非法添加其他物質的行為,同時亦會違反《消法》。根據該法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本條亦屬于為保護消費者權益所規定的懲罰性賠償條款。因此,當生產者或者經營者在食品中添加其他非法物質時,此時會構成《食品安全法》與《消法》的適用競合。由于上述二法所規定的請求權不能并用,故受有損害之消費者,在符合上述規定之情形時,只能選擇其中一法所規定之請求權行使。該選擇權性質為形成權,僅憑其單方意思表示即可使其與相對方之間的法律關系發生變化,且該權利一經行使不可撤回。
最后,知假買假行為會構成權利的濫用,不符合法律對于消費者人物性形象的描述。買假行為主體并非基于“為生活消費需要”之目的,其行為顯然是將《食品安全法》或者《消法》視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工具,與上述二法保護消費者權益之宗旨相悖。因此,該行為之效力會遭遇到立法之阻卻,即知假買假行為人無實體法上之懲罰性賠償請求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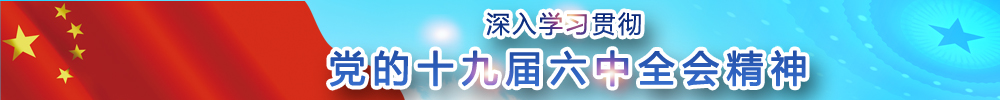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4432號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4432號